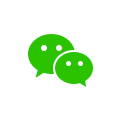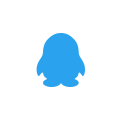童眼观戏|祖晴 为你朗诵

作者:琦君
朗诵:祖晴
有一次看评剧,台上演的是《芦花荡》,周瑜与张飞杀得难解难分。听后排一个小男孩问他爸爸:“这两个哪个是好人,哪个是坏人呀?”
做爸爸的回答:“两个都是好人呀。”
小孩又问:“两个好人为什么要打架呢?”
爸爸说:“好人跟好人,有时也会打架的,你不是有时也会跟哥哥打架吗?”
孩子不做声了。
过了一会儿,孩子又说:“爸爸,我不要跟哥哥打架了,我是好人,哥哥也是好人嘛!”
我听得乐不可支。
过了一阵,周瑜又与黄忠打了起来。
小孩又问:“爸爸,那个穿黄衣服的年轻人,胡子怎么这么白呀?”
爸爸说:“那是假胡子,他要扮老人呀。”
小孩说:“不要扮老人嘛,难看死了。”

我忍不住笑出声来,回头朝他看。他正用一条白围巾蒙住自己的下半边脸,模仿台上黄忠的白胡子。发现我在看他,他不好意思地放下围巾,噘起小嘴,说:“我不要白胡子,我不要当老人。”
我再也无心看台上的戏。我不禁想起自己年幼时,坐在外公的怀里看戏的情景。我最喜欢看诸葛亮与关公,他们一出来,我就合掌拜一拜。关公的马童一翻筋斗,我就拍手。我不喜欢周仓和张飞,他们的脸太大、太黑。
外公边看边讲笑话。他说,关公在台上,把桌子一拍,喊一声:“周仓在哪里?”周仓摘了胡子正在台下吃馄饨,听到关公喊他,连忙上台,忘了戴胡子。
关公一看他下巴光溜溜的,又把桌子一拍,说:“叫你爸爸来。”
周仓一摸下巴,连忙下去,把胡子戴了,再上来,喊一声“周仓来也”。
外公说完,边上的人都哈哈大笑。

最高兴的是第二天,戏班子全体到我家来游花园。我看出好几个人脸上的油彩都没洗干净,就问哪个是关公。
那个演关公的,指着自己的鼻子尖,说:“是我,是我。”
我说:“你是忠臣。我最讨厌曹操,他是奸臣。”
那个演曹操的大笑,说:“我是演奸臣的,你看我是好人还是坏人?”
我看他一脸和气,摇摇头,说:“我不知道。”
他说:“我也是好人呀。”
我说:“你不要演坏人嘛。”
他说:“都要演好人,坏人谁来演呢?”
我有点迷惘。
外公说:“台上的好人坏人你分得清 ,台下的好人坏人你就分不清咯。”
我越发糊涂了。
七八岁的童子,怎么懂得外公话里的意思?那时的我,不就跟现在后排那个孩子一样天真吗?

作者通过一台戏,将不同年纪的视角既矛盾又和谐的融合在一起。让人发现,台下的戏比台上的更为精彩,而人生的道理,也往往藏在这样或是那样不经意的小瞬间里。在文章的结尾,时光循环往复,眼前的孩子与年幼时的作者重合,带着对童真年代的怀念,带着如今对外公的话的了然,将人生与感悟压缩在这样的一方戏台上。
其实,戏与生活本就是一心同体,戏里戏外的都是人生。戏还是那台戏,变了的是我们,还有那不断向前的时间……

祖晴:中国儿童戏剧研究会理事,广东朗诵协会副会长,广东戏剧十佳中青年演员。曾在国际艺术节、全国戏剧节、省艺术节中多次获奖。为数千部集电影、电视剧、广播剧配音,主要配音作品:《喜羊羊与灰太狼》《芭啦啦小魔仙》《樱桃小丸子》等。
听音为你朗诵闻小语的作品《与一座古城对话》。